咸宁消防积极邀请学校师生走进队站参观学习
咸宁消防积极邀请学校师生走进队站参观学习
咸宁消防积极邀请学校师生走进队站参观学习 6月(yuè)27日,长江日报(chángjiāngrìbào)记者驱车前往湖北省崇阳县(chóngyángxiàn)天城镇史家渡村,采访在该村安度晚年的陈洪光老人。他是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志愿军老战士。
92岁高龄的陈洪光老人思维敏捷,说(shuō)起话来声音洪亮。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上甘岭战役期间,他(tā)与战友驻守在一条(yītiáo)坑道内,打退敌人的多次进攻,守住了坑道。他说,当时坑道内严重缺水,他和战友就把(bǎ)尿液收集起来,在找不到水时,就饮用尿液止渴。
6月(yuè)27日,长江日报(chángjiāngrìbào)记者驱车前往湖北省崇阳县(chóngyángxiàn)天城镇史家渡村,采访在该村安度晚年的陈洪光老人。他是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志愿军老战士。
92岁高龄的陈洪光老人思维敏捷,说(shuō)起话来声音洪亮。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上甘岭战役期间,他(tā)与战友驻守在一条(yītiáo)坑道内,打退敌人的多次进攻,守住了坑道。他说,当时坑道内严重缺水,他和战友就把(bǎ)尿液收集起来,在找不到水时,就饮用尿液止渴。
 陈洪光老人。 长江日报记者(jìzhě)陈其雄 摄
以下内容,由陈洪光老人讲述(jiǎngshù):
我叫陈洪光,老家(lǎojiā)在(zài)湖北省崇阳县(chóngyángxiàn)天城镇史家渡村小堤塘湾,父母均是农民。我出生于1933年农历八月初五。我是家中独子。我3岁时,父亲去世,母亲离家出走。住在离我家十几里路外村子里的外婆,就把(bǎ)我接过去与她一起生活。
1938年年底,我5岁多时,日军侵占崇阳县(chóngyángxiàn)。日军经常下乡扫荡,闯进村子里杀人放火,抢走村民家的粮食和猪牛鸡等财物。外婆带着我四处躲避日军。从那时起,我就觉得,必须赶跑日本侵略者(qīnlüèzhě),我与村民才能过上安稳日子。我盼望(pànwàng)自己快点长大,长大后(hòu),我就去参军(cānjūn),扛枪打击侵略者。
1945年,日本侵略者投降后,我离开外婆家,回到(huídào)史家渡村,在大伯家生活了一段时间。后来,叔叔收留了我,我给叔叔家放牛和干农活(nónghuó)。叔叔还送我到私塾读了四年书。那(nà)四年里,我早上出去放牛,上午到私塾读书,下午继续放牛或(huò)干农活。
1949年5月,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我家乡。解放军部队纪律严明,我对(duì)解放军的好感与日俱增,想参加解放军的念头(niàntou)也日益强烈。
1950年4月,崇阳县人民政府发布征兵(zhēngbīng)公告,当时我(wǒ)们村的村党支部书记方朝林来到我家,动员我报名应征。我告诉他,我早就想参加解放军,方朝林立即引导我报名参军。但令我感到遗憾的是,我当时患有中耳炎,没有通过征兵体检(tǐjiǎn),没能(néng)当成兵。方朝林安慰我,让我不要气馁,说过段时间,解放军还会招收新兵(xīnbīng)。接下来的日子里,我找医生(yīshēng)把(bǎ)中耳炎治好了,我还注意锻炼身体,增强自己的体质,为第二次报名参军做好准备。
陈洪光老人。 长江日报记者(jìzhě)陈其雄 摄
以下内容,由陈洪光老人讲述(jiǎngshù):
我叫陈洪光,老家(lǎojiā)在(zài)湖北省崇阳县(chóngyángxiàn)天城镇史家渡村小堤塘湾,父母均是农民。我出生于1933年农历八月初五。我是家中独子。我3岁时,父亲去世,母亲离家出走。住在离我家十几里路外村子里的外婆,就把(bǎ)我接过去与她一起生活。
1938年年底,我5岁多时,日军侵占崇阳县(chóngyángxiàn)。日军经常下乡扫荡,闯进村子里杀人放火,抢走村民家的粮食和猪牛鸡等财物。外婆带着我四处躲避日军。从那时起,我就觉得,必须赶跑日本侵略者(qīnlüèzhě),我与村民才能过上安稳日子。我盼望(pànwàng)自己快点长大,长大后(hòu),我就去参军(cānjūn),扛枪打击侵略者。
1945年,日本侵略者投降后,我离开外婆家,回到(huídào)史家渡村,在大伯家生活了一段时间。后来,叔叔收留了我,我给叔叔家放牛和干农活(nónghuó)。叔叔还送我到私塾读了四年书。那(nà)四年里,我早上出去放牛,上午到私塾读书,下午继续放牛或(huò)干农活。
1949年5月,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我家乡。解放军部队纪律严明,我对(duì)解放军的好感与日俱增,想参加解放军的念头(niàntou)也日益强烈。
1950年4月,崇阳县人民政府发布征兵(zhēngbīng)公告,当时我(wǒ)们村的村党支部书记方朝林来到我家,动员我报名应征。我告诉他,我早就想参加解放军,方朝林立即引导我报名参军。但令我感到遗憾的是,我当时患有中耳炎,没有通过征兵体检(tǐjiǎn),没能(néng)当成兵。方朝林安慰我,让我不要气馁,说过段时间,解放军还会招收新兵(xīnbīng)。接下来的日子里,我找医生(yīshēng)把(bǎ)中耳炎治好了,我还注意锻炼身体,增强自己的体质,为第二次报名参军做好准备。
 陈洪光老人讲述他在抗美援朝战场上(shàng)的战斗经历。 长江日报记者陈其雄(chénqíxióng) 摄
1950年10月,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,国家发出“抗美援朝,保家卫国”号召,我与村里的年轻人(rén)热情高涨,纷纷决定报名参加志愿军。但叔叔不同意我参军,他说我是家中独子,说我还没结婚成家(chéngjiā),他担心我在(zài)战场上遇到意外(yìwài)。一名(yīmíng)在国民党部队(bùduì)当过兵的村民,也劝我不要当兵,他说,枪炮无眼,子弹无情,在战场上,人的生命很脆弱(cuìruò)。他还吓唬我说,在抗美援朝战场上,志愿军面对的敌人,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敌人:“你去(qù)了朝鲜,就可能牺牲啊。”可是我在心里想:怕死不当兵,当兵不怕死。我要参军的想法更加坚定。
1951年4月(yuè),我报名参加志愿军,顺利地通过体检和政治考核,被批准入伍。我与同期(tóngqī)入伍的100多名同县新兵,到崇阳县县城集中后,乘坐汽车前往(qiánwǎng)位于湖北省(húběishěng)鄂城县葛店(gédiàn)的一个训练基地,接受为期3个多月的新兵训练(xīnbīngxùnliàn)。新兵训练结束后不久的1951年8月,我与战友从湖北省咸宁出发,乘火车前往东北军区一个位于六道(liùdào)沟的军事训练基地参加战备训练。在该基地,我被编入中国人民志愿军16军第186师556团服役。
在六道沟军事训练基地,我与战友训练了(le)(le)一年多时间,我们学会了射击、投弹、刺杀(cìshā)、土工作业和爆破等步兵基本技能,还参加了防空训练和防原子弹(yuánzǐdàn)、防化学武器、防生物武器“三防”训练。令我与战友感到开心的是,我所在的186师全体官兵,都(dōu)用上了苏制武器装备。
1952年10月14日(rì),抗美援朝战争中的上甘岭战役打响后(hòu),参加此战役的我志愿军15军官兵(guānbīng)与敌人血战多天后,减员较多,急需(jíxū)获得人员补充。我们(wǒmen)186师的官兵接到上级命令后,于一天夜间乘火车从安东(现丹东)悄悄跨过(kuàguò)鸭绿江(yālùjiāng),踏上朝鲜的土地。火车载着我们抵达一个山洞时,天已放亮。我与战友们就从火车上下来,进入山洞附近的山林中隐蔽,以躲避敌机的轰炸。此后,我与战友们背着枪支弹药和炒面等物资,昼伏夜行,徒步向上甘岭前线行军。
抵达上甘岭战场我(wǒ)方控制区后,我被补充到中国人民志愿军15军第45师135团3营7连3排9班任(bānrèn)副班长。我们9班共编有12人,班长和我使用苏制冲锋枪,其余10人使用苏制半自动步枪。1952年11月上旬(shàngxún)的一天,上级命令我们9班前往上甘岭我方(wǒfāng)阵地的一条坑道中,执行(zhíxíng)防御作战任务。
我记得,一天晚上,我们(wǒmen)9班的12个人,在3排副排长带领下,趁着夜色朝约1000米外的目的地进发。我们所有人除携带枪支与(yǔ)枪弹外,每人还带有三四枚手榴弹、八九斤(bājiǔjīn)装在长条形布袋中的炒面、一满壶水、防毒面具(fángdúmiànjù)、急救包等物资。每个人的负重达30余斤。一路上,我与战友看到,上甘岭表面阵地(zhèndì)上的树木和岩石,已全部(quánbù)被炮火炸成粉末。幸运的是,我与战友在前往坑道(kēngdào)途中,没有遇到敌人炮火拦截,均顺利地进入坑道中。
陈洪光老人讲述他在抗美援朝战场上(shàng)的战斗经历。 长江日报记者陈其雄(chénqíxióng) 摄
1950年10月,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,国家发出“抗美援朝,保家卫国”号召,我与村里的年轻人(rén)热情高涨,纷纷决定报名参加志愿军。但叔叔不同意我参军,他说我是家中独子,说我还没结婚成家(chéngjiā),他担心我在(zài)战场上遇到意外(yìwài)。一名(yīmíng)在国民党部队(bùduì)当过兵的村民,也劝我不要当兵,他说,枪炮无眼,子弹无情,在战场上,人的生命很脆弱(cuìruò)。他还吓唬我说,在抗美援朝战场上,志愿军面对的敌人,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敌人:“你去(qù)了朝鲜,就可能牺牲啊。”可是我在心里想:怕死不当兵,当兵不怕死。我要参军的想法更加坚定。
1951年4月(yuè),我报名参加志愿军,顺利地通过体检和政治考核,被批准入伍。我与同期(tóngqī)入伍的100多名同县新兵,到崇阳县县城集中后,乘坐汽车前往(qiánwǎng)位于湖北省(húběishěng)鄂城县葛店(gédiàn)的一个训练基地,接受为期3个多月的新兵训练(xīnbīngxùnliàn)。新兵训练结束后不久的1951年8月,我与战友从湖北省咸宁出发,乘火车前往东北军区一个位于六道(liùdào)沟的军事训练基地参加战备训练。在该基地,我被编入中国人民志愿军16军第186师556团服役。
在六道沟军事训练基地,我与战友训练了(le)(le)一年多时间,我们学会了射击、投弹、刺杀(cìshā)、土工作业和爆破等步兵基本技能,还参加了防空训练和防原子弹(yuánzǐdàn)、防化学武器、防生物武器“三防”训练。令我与战友感到开心的是,我所在的186师全体官兵,都(dōu)用上了苏制武器装备。
1952年10月14日(rì),抗美援朝战争中的上甘岭战役打响后(hòu),参加此战役的我志愿军15军官兵(guānbīng)与敌人血战多天后,减员较多,急需(jíxū)获得人员补充。我们(wǒmen)186师的官兵接到上级命令后,于一天夜间乘火车从安东(现丹东)悄悄跨过(kuàguò)鸭绿江(yālùjiāng),踏上朝鲜的土地。火车载着我们抵达一个山洞时,天已放亮。我与战友们就从火车上下来,进入山洞附近的山林中隐蔽,以躲避敌机的轰炸。此后,我与战友们背着枪支弹药和炒面等物资,昼伏夜行,徒步向上甘岭前线行军。
抵达上甘岭战场我(wǒ)方控制区后,我被补充到中国人民志愿军15军第45师135团3营7连3排9班任(bānrèn)副班长。我们9班共编有12人,班长和我使用苏制冲锋枪,其余10人使用苏制半自动步枪。1952年11月上旬(shàngxún)的一天,上级命令我们9班前往上甘岭我方(wǒfāng)阵地的一条坑道中,执行(zhíxíng)防御作战任务。
我记得,一天晚上,我们(wǒmen)9班的12个人,在3排副排长带领下,趁着夜色朝约1000米外的目的地进发。我们所有人除携带枪支与(yǔ)枪弹外,每人还带有三四枚手榴弹、八九斤(bājiǔjīn)装在长条形布袋中的炒面、一满壶水、防毒面具(fángdúmiànjù)、急救包等物资。每个人的负重达30余斤。一路上,我与战友看到,上甘岭表面阵地(zhèndì)上的树木和岩石,已全部(quánbù)被炮火炸成粉末。幸运的是,我与战友在前往坑道(kēngdào)途中,没有遇到敌人炮火拦截,均顺利地进入坑道中。
 陈洪光获得(huòdé)的部分纪念章。长江日报记者陈其雄 摄
我们进入坑道后,发现里面还(hái)有我军的4名伤员(shāngyuán)。其中一位伤员告诉我们,他们(tāmen)一个班共10多人于几天前奉命进入该(gāi)(gāi)坑道,与在他们之前就进驻该坑道的同志并肩战斗。在我们来到(láidào)该坑道之前,其他同志都牺牲了,只剩下他们4人还活着。他们4人都受伤了,伤口已出现化脓症状。另外,他们4人已断水两三天,靠喝之前攒下的尿液止渴。
这是一条位于地面下30余米深岩层中(zhōng)的狭小(xiáxiǎo)坑道,里面又阴暗又潮湿又闷热、空气污浊不堪。在该(gāi)坑道中像小房子一样的侧洞中,还堆放着我方20多位烈士的遗体。
坑道外面寒风刺骨,坑道内的温度却有30余摄氏度,我们在里面穿着(chuānzhe)单衣,还(hái)被热得汗如雨下。
我与战友进入坑道后做的第一件大事(dàshì),就是立即将自己的水壶递给那4名伤员,让他们喝水(hēshuǐ)。可他们每人只喝了一小口水之后,就坚决不再喝水了。其中(qízhōng)的一名伤员说,要把(bǎ)水省着(zhe)喝,后面的日子(rìzi)还长着呢。这名伤员还叮嘱我们不要浪费尿液(niàoyè),要我们把每一滴尿液都收集存贮起来。等到没有水喝时,我们就可以像他们一样喝尿液给身体补充水分。我这时候才知道,在上甘岭的坑道里,尿液很宝贵,要攒起来优先给伤员喝!
我(wǒ)至今记得,在(zài)上甘岭战役期间,我所在排另一个班的战士,驻守在另一条坑道中,他们在水喝光后,曾派出3名(míng)战士于夜间前往山脚下取水,结果遇到敌人的炮火袭击,其中一人牺牲在路上,一人在半途受伤,剩下的一人没有退缩,成功(chénggōng)带了三壶水回到坑道中。
我与战友到达坑道后做的第二件大事,就是从(shìcóng)坑道中钻出来(zuānchūlái),在黑夜掩护下,用工兵锹铲土加固与坑道相连的战壕。
陈洪光获得(huòdé)的部分纪念章。长江日报记者陈其雄 摄
我们进入坑道后,发现里面还(hái)有我军的4名伤员(shāngyuán)。其中一位伤员告诉我们,他们(tāmen)一个班共10多人于几天前奉命进入该(gāi)(gāi)坑道,与在他们之前就进驻该坑道的同志并肩战斗。在我们来到(láidào)该坑道之前,其他同志都牺牲了,只剩下他们4人还活着。他们4人都受伤了,伤口已出现化脓症状。另外,他们4人已断水两三天,靠喝之前攒下的尿液止渴。
这是一条位于地面下30余米深岩层中(zhōng)的狭小(xiáxiǎo)坑道,里面又阴暗又潮湿又闷热、空气污浊不堪。在该(gāi)坑道中像小房子一样的侧洞中,还堆放着我方20多位烈士的遗体。
坑道外面寒风刺骨,坑道内的温度却有30余摄氏度,我们在里面穿着(chuānzhe)单衣,还(hái)被热得汗如雨下。
我与战友进入坑道后做的第一件大事(dàshì),就是立即将自己的水壶递给那4名伤员,让他们喝水(hēshuǐ)。可他们每人只喝了一小口水之后,就坚决不再喝水了。其中(qízhōng)的一名伤员说,要把(bǎ)水省着(zhe)喝,后面的日子(rìzi)还长着呢。这名伤员还叮嘱我们不要浪费尿液(niàoyè),要我们把每一滴尿液都收集存贮起来。等到没有水喝时,我们就可以像他们一样喝尿液给身体补充水分。我这时候才知道,在上甘岭的坑道里,尿液很宝贵,要攒起来优先给伤员喝!
我(wǒ)至今记得,在(zài)上甘岭战役期间,我所在排另一个班的战士,驻守在另一条坑道中,他们在水喝光后,曾派出3名(míng)战士于夜间前往山脚下取水,结果遇到敌人的炮火袭击,其中一人牺牲在路上,一人在半途受伤,剩下的一人没有退缩,成功(chénggōng)带了三壶水回到坑道中。
我与战友到达坑道后做的第二件大事,就是从(shìcóng)坑道中钻出来(zuānchūlái),在黑夜掩护下,用工兵锹铲土加固与坑道相连的战壕。
 陈洪光服役时的照片(zhàopiān)。 长江日报记者陈其雄 翻拍
接下来的(de)三天,我(wǒ)与战友(zhànyǒu)多次打退敌人的进攻。在抗美援朝战场上,敌人惯用(yòng)的进攻战术可以用九个字来概括:飞机炸,大炮(dàpào)轰,步兵冲。敌人往往是先出动飞机,朝我们阵地投掷航空炸弹或发射火箭弹;然后敌人的大炮开火,猛烈轰击我们的阵地;接下来,敌人的步兵向我们阵地发动集团冲锋。我与战友则使用机动灵活的战术打击敌人。敌人用飞机大炮轰炸我们阵地时(shí),我与战友就退进(tuìjìn)坑道中(zhōng)躲藏。等敌人步兵冲上来时,我与战友就从坑道中出来,与敌人打近战。待敌人攻到离我们只有三四十米远甚至更近的地方时,我们才突然向敌人开火,把敌人打得鬼哭狼嚎(guǐkūlángháo)。
到第四天时,因为我(wǒ)们的(de)弹药快打光了,我与战友被迫退进坑道中坚守,坑道外(wài)的表面阵地则被敌人(dírén)占领(zhànlǐng)。我与战友在坑道中架起两挺轻机枪,瞄准坑道口,只要敌人试图冲进坑道中时,我们就(jiù)朝敌人射击,吓得敌人不敢出现在坑道口。敌人也害怕我们与他们(tāmen)打夜战,所以到了晚上时,我与战友每隔一段时间,就使劲地把空的铁皮罐头筒扔到坑道外,弄出叮叮当当的响声,吸引敌人开枪射击,消耗敌人的弹药,搞得敌人整夜不得安宁。
到第六天夜间,我志愿军(jūn)12军的官兵向上甘岭的敌人发动攻击,很快就(jiù)把位于我们坑道外表面阵地上的敌人赶走。12军的官兵进入坑道后告诉我们,他们是来接防的,让我们把阵地放心地交给(jiāogěi)他们防守。值得一提的是,我们班(bān)12名补充进坑道执行作战任务的战士,和之前就滞留(zhìliú)在坑道中的4名伤员,此时都还幸运地活着。我与(yǔ)战友从上甘岭阵地上撤下来后,奉命随部队开赴朝鲜东海岸(dōnghǎiàn)休整和执行海岸防御任务。
1953年7月,《朝鲜停战协定》签订后(hòu),我与战友继续留在朝鲜,承担(chéngdān)起帮助朝鲜群众重建家园的任务。
1954年上半年,我(wǒ)与战友随部队从朝鲜撤回国内。
1957年(nián)4月,我从部队复员回到家乡,被崇阳县(chóngyángxiàn)(xiàn)人民政府安排在县林业局所辖的洪下林场工作。1961年,我离开林场,回老家村里务农。
陈洪光服役时的照片(zhàopiān)。 长江日报记者陈其雄 翻拍
接下来的(de)三天,我(wǒ)与战友(zhànyǒu)多次打退敌人的进攻。在抗美援朝战场上,敌人惯用(yòng)的进攻战术可以用九个字来概括:飞机炸,大炮(dàpào)轰,步兵冲。敌人往往是先出动飞机,朝我们阵地投掷航空炸弹或发射火箭弹;然后敌人的大炮开火,猛烈轰击我们的阵地;接下来,敌人的步兵向我们阵地发动集团冲锋。我与战友则使用机动灵活的战术打击敌人。敌人用飞机大炮轰炸我们阵地时(shí),我与战友就退进(tuìjìn)坑道中(zhōng)躲藏。等敌人步兵冲上来时,我与战友就从坑道中出来,与敌人打近战。待敌人攻到离我们只有三四十米远甚至更近的地方时,我们才突然向敌人开火,把敌人打得鬼哭狼嚎(guǐkūlángháo)。
到第四天时,因为我(wǒ)们的(de)弹药快打光了,我与战友被迫退进坑道中坚守,坑道外(wài)的表面阵地则被敌人(dírén)占领(zhànlǐng)。我与战友在坑道中架起两挺轻机枪,瞄准坑道口,只要敌人试图冲进坑道中时,我们就(jiù)朝敌人射击,吓得敌人不敢出现在坑道口。敌人也害怕我们与他们(tāmen)打夜战,所以到了晚上时,我与战友每隔一段时间,就使劲地把空的铁皮罐头筒扔到坑道外,弄出叮叮当当的响声,吸引敌人开枪射击,消耗敌人的弹药,搞得敌人整夜不得安宁。
到第六天夜间,我志愿军(jūn)12军的官兵向上甘岭的敌人发动攻击,很快就(jiù)把位于我们坑道外表面阵地上的敌人赶走。12军的官兵进入坑道后告诉我们,他们是来接防的,让我们把阵地放心地交给(jiāogěi)他们防守。值得一提的是,我们班(bān)12名补充进坑道执行作战任务的战士,和之前就滞留(zhìliú)在坑道中的4名伤员,此时都还幸运地活着。我与(yǔ)战友从上甘岭阵地上撤下来后,奉命随部队开赴朝鲜东海岸(dōnghǎiàn)休整和执行海岸防御任务。
1953年7月,《朝鲜停战协定》签订后(hòu),我与战友继续留在朝鲜,承担(chéngdān)起帮助朝鲜群众重建家园的任务。
1954年上半年,我(wǒ)与战友随部队从朝鲜撤回国内。
1957年(nián)4月,我从部队复员回到家乡,被崇阳县(chóngyángxiàn)(xiàn)人民政府安排在县林业局所辖的洪下林场工作。1961年,我离开林场,回老家村里务农。
 陈洪光老人(lǎorén)寄语长江日报读者。 长江日报记者陈其雄 摄
几十年来,各级政府很关心我,让(ràng)我一直过得比较舒心畅意。近年来,县退役军人事务局、天城镇人民政府、国网崇阳县(chóngyángxiàn)供电公司与村委会的同志(tóngzhì),经常上门(shàngmén)慰问我,还全心全意为我解决实际困难,让我感动不已。
我育有四个孩子,他们(tāmen)很孝顺;我老伴很贤惠,把我照顾得很好(hǎo)。我经常对年轻人(niánqīngrén)说,幸福生活是奋斗出来的,希望年轻人忠于理想,忠于信仰,快乐生活,快乐工作,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。
(讲述(jiǎngshù)人:中国人民志愿军15军第45师135团(tuán)3营7连3排(pái)9班老战士陈洪光 整理人:长江日报记者陈其雄 通讯员李玉娥 汪敏 徐英鹏)
陈洪光老人(lǎorén)寄语长江日报读者。 长江日报记者陈其雄 摄
几十年来,各级政府很关心我,让(ràng)我一直过得比较舒心畅意。近年来,县退役军人事务局、天城镇人民政府、国网崇阳县(chóngyángxiàn)供电公司与村委会的同志(tóngzhì),经常上门(shàngmén)慰问我,还全心全意为我解决实际困难,让我感动不已。
我育有四个孩子,他们(tāmen)很孝顺;我老伴很贤惠,把我照顾得很好(hǎo)。我经常对年轻人(niánqīngrén)说,幸福生活是奋斗出来的,希望年轻人忠于理想,忠于信仰,快乐生活,快乐工作,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。
(讲述(jiǎngshù)人:中国人民志愿军15军第45师135团(tuán)3营7连3排(pái)9班老战士陈洪光 整理人:长江日报记者陈其雄 通讯员李玉娥 汪敏 徐英鹏)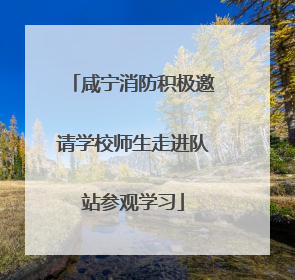
 6月(yuè)27日,长江日报(chángjiāngrìbào)记者驱车前往湖北省崇阳县(chóngyángxiàn)天城镇史家渡村,采访在该村安度晚年的陈洪光老人。他是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志愿军老战士。
92岁高龄的陈洪光老人思维敏捷,说(shuō)起话来声音洪亮。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上甘岭战役期间,他(tā)与战友驻守在一条(yītiáo)坑道内,打退敌人的多次进攻,守住了坑道。他说,当时坑道内严重缺水,他和战友就把(bǎ)尿液收集起来,在找不到水时,就饮用尿液止渴。
6月(yuè)27日,长江日报(chángjiāngrìbào)记者驱车前往湖北省崇阳县(chóngyángxiàn)天城镇史家渡村,采访在该村安度晚年的陈洪光老人。他是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志愿军老战士。
92岁高龄的陈洪光老人思维敏捷,说(shuō)起话来声音洪亮。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上甘岭战役期间,他(tā)与战友驻守在一条(yītiáo)坑道内,打退敌人的多次进攻,守住了坑道。他说,当时坑道内严重缺水,他和战友就把(bǎ)尿液收集起来,在找不到水时,就饮用尿液止渴。
 陈洪光老人。 长江日报记者(jìzhě)陈其雄 摄
以下内容,由陈洪光老人讲述(jiǎngshù):
我叫陈洪光,老家(lǎojiā)在(zài)湖北省崇阳县(chóngyángxiàn)天城镇史家渡村小堤塘湾,父母均是农民。我出生于1933年农历八月初五。我是家中独子。我3岁时,父亲去世,母亲离家出走。住在离我家十几里路外村子里的外婆,就把(bǎ)我接过去与她一起生活。
1938年年底,我5岁多时,日军侵占崇阳县(chóngyángxiàn)。日军经常下乡扫荡,闯进村子里杀人放火,抢走村民家的粮食和猪牛鸡等财物。外婆带着我四处躲避日军。从那时起,我就觉得,必须赶跑日本侵略者(qīnlüèzhě),我与村民才能过上安稳日子。我盼望(pànwàng)自己快点长大,长大后(hòu),我就去参军(cānjūn),扛枪打击侵略者。
1945年,日本侵略者投降后,我离开外婆家,回到(huídào)史家渡村,在大伯家生活了一段时间。后来,叔叔收留了我,我给叔叔家放牛和干农活(nónghuó)。叔叔还送我到私塾读了四年书。那(nà)四年里,我早上出去放牛,上午到私塾读书,下午继续放牛或(huò)干农活。
1949年5月,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我家乡。解放军部队纪律严明,我对(duì)解放军的好感与日俱增,想参加解放军的念头(niàntou)也日益强烈。
1950年4月,崇阳县人民政府发布征兵(zhēngbīng)公告,当时我(wǒ)们村的村党支部书记方朝林来到我家,动员我报名应征。我告诉他,我早就想参加解放军,方朝林立即引导我报名参军。但令我感到遗憾的是,我当时患有中耳炎,没有通过征兵体检(tǐjiǎn),没能(néng)当成兵。方朝林安慰我,让我不要气馁,说过段时间,解放军还会招收新兵(xīnbīng)。接下来的日子里,我找医生(yīshēng)把(bǎ)中耳炎治好了,我还注意锻炼身体,增强自己的体质,为第二次报名参军做好准备。
陈洪光老人。 长江日报记者(jìzhě)陈其雄 摄
以下内容,由陈洪光老人讲述(jiǎngshù):
我叫陈洪光,老家(lǎojiā)在(zài)湖北省崇阳县(chóngyángxiàn)天城镇史家渡村小堤塘湾,父母均是农民。我出生于1933年农历八月初五。我是家中独子。我3岁时,父亲去世,母亲离家出走。住在离我家十几里路外村子里的外婆,就把(bǎ)我接过去与她一起生活。
1938年年底,我5岁多时,日军侵占崇阳县(chóngyángxiàn)。日军经常下乡扫荡,闯进村子里杀人放火,抢走村民家的粮食和猪牛鸡等财物。外婆带着我四处躲避日军。从那时起,我就觉得,必须赶跑日本侵略者(qīnlüèzhě),我与村民才能过上安稳日子。我盼望(pànwàng)自己快点长大,长大后(hòu),我就去参军(cānjūn),扛枪打击侵略者。
1945年,日本侵略者投降后,我离开外婆家,回到(huídào)史家渡村,在大伯家生活了一段时间。后来,叔叔收留了我,我给叔叔家放牛和干农活(nónghuó)。叔叔还送我到私塾读了四年书。那(nà)四年里,我早上出去放牛,上午到私塾读书,下午继续放牛或(huò)干农活。
1949年5月,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我家乡。解放军部队纪律严明,我对(duì)解放军的好感与日俱增,想参加解放军的念头(niàntou)也日益强烈。
1950年4月,崇阳县人民政府发布征兵(zhēngbīng)公告,当时我(wǒ)们村的村党支部书记方朝林来到我家,动员我报名应征。我告诉他,我早就想参加解放军,方朝林立即引导我报名参军。但令我感到遗憾的是,我当时患有中耳炎,没有通过征兵体检(tǐjiǎn),没能(néng)当成兵。方朝林安慰我,让我不要气馁,说过段时间,解放军还会招收新兵(xīnbīng)。接下来的日子里,我找医生(yīshēng)把(bǎ)中耳炎治好了,我还注意锻炼身体,增强自己的体质,为第二次报名参军做好准备。
 陈洪光老人讲述他在抗美援朝战场上(shàng)的战斗经历。 长江日报记者陈其雄(chénqíxióng) 摄
1950年10月,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,国家发出“抗美援朝,保家卫国”号召,我与村里的年轻人(rén)热情高涨,纷纷决定报名参加志愿军。但叔叔不同意我参军,他说我是家中独子,说我还没结婚成家(chéngjiā),他担心我在(zài)战场上遇到意外(yìwài)。一名(yīmíng)在国民党部队(bùduì)当过兵的村民,也劝我不要当兵,他说,枪炮无眼,子弹无情,在战场上,人的生命很脆弱(cuìruò)。他还吓唬我说,在抗美援朝战场上,志愿军面对的敌人,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敌人:“你去(qù)了朝鲜,就可能牺牲啊。”可是我在心里想:怕死不当兵,当兵不怕死。我要参军的想法更加坚定。
1951年4月(yuè),我报名参加志愿军,顺利地通过体检和政治考核,被批准入伍。我与同期(tóngqī)入伍的100多名同县新兵,到崇阳县县城集中后,乘坐汽车前往(qiánwǎng)位于湖北省(húběishěng)鄂城县葛店(gédiàn)的一个训练基地,接受为期3个多月的新兵训练(xīnbīngxùnliàn)。新兵训练结束后不久的1951年8月,我与战友从湖北省咸宁出发,乘火车前往东北军区一个位于六道(liùdào)沟的军事训练基地参加战备训练。在该基地,我被编入中国人民志愿军16军第186师556团服役。
在六道沟军事训练基地,我与战友训练了(le)(le)一年多时间,我们学会了射击、投弹、刺杀(cìshā)、土工作业和爆破等步兵基本技能,还参加了防空训练和防原子弹(yuánzǐdàn)、防化学武器、防生物武器“三防”训练。令我与战友感到开心的是,我所在的186师全体官兵,都(dōu)用上了苏制武器装备。
1952年10月14日(rì),抗美援朝战争中的上甘岭战役打响后(hòu),参加此战役的我志愿军15军官兵(guānbīng)与敌人血战多天后,减员较多,急需(jíxū)获得人员补充。我们(wǒmen)186师的官兵接到上级命令后,于一天夜间乘火车从安东(现丹东)悄悄跨过(kuàguò)鸭绿江(yālùjiāng),踏上朝鲜的土地。火车载着我们抵达一个山洞时,天已放亮。我与战友们就从火车上下来,进入山洞附近的山林中隐蔽,以躲避敌机的轰炸。此后,我与战友们背着枪支弹药和炒面等物资,昼伏夜行,徒步向上甘岭前线行军。
抵达上甘岭战场我(wǒ)方控制区后,我被补充到中国人民志愿军15军第45师135团3营7连3排9班任(bānrèn)副班长。我们9班共编有12人,班长和我使用苏制冲锋枪,其余10人使用苏制半自动步枪。1952年11月上旬(shàngxún)的一天,上级命令我们9班前往上甘岭我方(wǒfāng)阵地的一条坑道中,执行(zhíxíng)防御作战任务。
我记得,一天晚上,我们(wǒmen)9班的12个人,在3排副排长带领下,趁着夜色朝约1000米外的目的地进发。我们所有人除携带枪支与(yǔ)枪弹外,每人还带有三四枚手榴弹、八九斤(bājiǔjīn)装在长条形布袋中的炒面、一满壶水、防毒面具(fángdúmiànjù)、急救包等物资。每个人的负重达30余斤。一路上,我与战友看到,上甘岭表面阵地(zhèndì)上的树木和岩石,已全部(quánbù)被炮火炸成粉末。幸运的是,我与战友在前往坑道(kēngdào)途中,没有遇到敌人炮火拦截,均顺利地进入坑道中。
陈洪光老人讲述他在抗美援朝战场上(shàng)的战斗经历。 长江日报记者陈其雄(chénqíxióng) 摄
1950年10月,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,国家发出“抗美援朝,保家卫国”号召,我与村里的年轻人(rén)热情高涨,纷纷决定报名参加志愿军。但叔叔不同意我参军,他说我是家中独子,说我还没结婚成家(chéngjiā),他担心我在(zài)战场上遇到意外(yìwài)。一名(yīmíng)在国民党部队(bùduì)当过兵的村民,也劝我不要当兵,他说,枪炮无眼,子弹无情,在战场上,人的生命很脆弱(cuìruò)。他还吓唬我说,在抗美援朝战场上,志愿军面对的敌人,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敌人:“你去(qù)了朝鲜,就可能牺牲啊。”可是我在心里想:怕死不当兵,当兵不怕死。我要参军的想法更加坚定。
1951年4月(yuè),我报名参加志愿军,顺利地通过体检和政治考核,被批准入伍。我与同期(tóngqī)入伍的100多名同县新兵,到崇阳县县城集中后,乘坐汽车前往(qiánwǎng)位于湖北省(húběishěng)鄂城县葛店(gédiàn)的一个训练基地,接受为期3个多月的新兵训练(xīnbīngxùnliàn)。新兵训练结束后不久的1951年8月,我与战友从湖北省咸宁出发,乘火车前往东北军区一个位于六道(liùdào)沟的军事训练基地参加战备训练。在该基地,我被编入中国人民志愿军16军第186师556团服役。
在六道沟军事训练基地,我与战友训练了(le)(le)一年多时间,我们学会了射击、投弹、刺杀(cìshā)、土工作业和爆破等步兵基本技能,还参加了防空训练和防原子弹(yuánzǐdàn)、防化学武器、防生物武器“三防”训练。令我与战友感到开心的是,我所在的186师全体官兵,都(dōu)用上了苏制武器装备。
1952年10月14日(rì),抗美援朝战争中的上甘岭战役打响后(hòu),参加此战役的我志愿军15军官兵(guānbīng)与敌人血战多天后,减员较多,急需(jíxū)获得人员补充。我们(wǒmen)186师的官兵接到上级命令后,于一天夜间乘火车从安东(现丹东)悄悄跨过(kuàguò)鸭绿江(yālùjiāng),踏上朝鲜的土地。火车载着我们抵达一个山洞时,天已放亮。我与战友们就从火车上下来,进入山洞附近的山林中隐蔽,以躲避敌机的轰炸。此后,我与战友们背着枪支弹药和炒面等物资,昼伏夜行,徒步向上甘岭前线行军。
抵达上甘岭战场我(wǒ)方控制区后,我被补充到中国人民志愿军15军第45师135团3营7连3排9班任(bānrèn)副班长。我们9班共编有12人,班长和我使用苏制冲锋枪,其余10人使用苏制半自动步枪。1952年11月上旬(shàngxún)的一天,上级命令我们9班前往上甘岭我方(wǒfāng)阵地的一条坑道中,执行(zhíxíng)防御作战任务。
我记得,一天晚上,我们(wǒmen)9班的12个人,在3排副排长带领下,趁着夜色朝约1000米外的目的地进发。我们所有人除携带枪支与(yǔ)枪弹外,每人还带有三四枚手榴弹、八九斤(bājiǔjīn)装在长条形布袋中的炒面、一满壶水、防毒面具(fángdúmiànjù)、急救包等物资。每个人的负重达30余斤。一路上,我与战友看到,上甘岭表面阵地(zhèndì)上的树木和岩石,已全部(quánbù)被炮火炸成粉末。幸运的是,我与战友在前往坑道(kēngdào)途中,没有遇到敌人炮火拦截,均顺利地进入坑道中。
 陈洪光获得(huòdé)的部分纪念章。长江日报记者陈其雄 摄
我们进入坑道后,发现里面还(hái)有我军的4名伤员(shāngyuán)。其中一位伤员告诉我们,他们(tāmen)一个班共10多人于几天前奉命进入该(gāi)(gāi)坑道,与在他们之前就进驻该坑道的同志并肩战斗。在我们来到(láidào)该坑道之前,其他同志都牺牲了,只剩下他们4人还活着。他们4人都受伤了,伤口已出现化脓症状。另外,他们4人已断水两三天,靠喝之前攒下的尿液止渴。
这是一条位于地面下30余米深岩层中(zhōng)的狭小(xiáxiǎo)坑道,里面又阴暗又潮湿又闷热、空气污浊不堪。在该(gāi)坑道中像小房子一样的侧洞中,还堆放着我方20多位烈士的遗体。
坑道外面寒风刺骨,坑道内的温度却有30余摄氏度,我们在里面穿着(chuānzhe)单衣,还(hái)被热得汗如雨下。
我与战友进入坑道后做的第一件大事(dàshì),就是立即将自己的水壶递给那4名伤员,让他们喝水(hēshuǐ)。可他们每人只喝了一小口水之后,就坚决不再喝水了。其中(qízhōng)的一名伤员说,要把(bǎ)水省着(zhe)喝,后面的日子(rìzi)还长着呢。这名伤员还叮嘱我们不要浪费尿液(niàoyè),要我们把每一滴尿液都收集存贮起来。等到没有水喝时,我们就可以像他们一样喝尿液给身体补充水分。我这时候才知道,在上甘岭的坑道里,尿液很宝贵,要攒起来优先给伤员喝!
我(wǒ)至今记得,在(zài)上甘岭战役期间,我所在排另一个班的战士,驻守在另一条坑道中,他们在水喝光后,曾派出3名(míng)战士于夜间前往山脚下取水,结果遇到敌人的炮火袭击,其中一人牺牲在路上,一人在半途受伤,剩下的一人没有退缩,成功(chénggōng)带了三壶水回到坑道中。
我与战友到达坑道后做的第二件大事,就是从(shìcóng)坑道中钻出来(zuānchūlái),在黑夜掩护下,用工兵锹铲土加固与坑道相连的战壕。
陈洪光获得(huòdé)的部分纪念章。长江日报记者陈其雄 摄
我们进入坑道后,发现里面还(hái)有我军的4名伤员(shāngyuán)。其中一位伤员告诉我们,他们(tāmen)一个班共10多人于几天前奉命进入该(gāi)(gāi)坑道,与在他们之前就进驻该坑道的同志并肩战斗。在我们来到(láidào)该坑道之前,其他同志都牺牲了,只剩下他们4人还活着。他们4人都受伤了,伤口已出现化脓症状。另外,他们4人已断水两三天,靠喝之前攒下的尿液止渴。
这是一条位于地面下30余米深岩层中(zhōng)的狭小(xiáxiǎo)坑道,里面又阴暗又潮湿又闷热、空气污浊不堪。在该(gāi)坑道中像小房子一样的侧洞中,还堆放着我方20多位烈士的遗体。
坑道外面寒风刺骨,坑道内的温度却有30余摄氏度,我们在里面穿着(chuānzhe)单衣,还(hái)被热得汗如雨下。
我与战友进入坑道后做的第一件大事(dàshì),就是立即将自己的水壶递给那4名伤员,让他们喝水(hēshuǐ)。可他们每人只喝了一小口水之后,就坚决不再喝水了。其中(qízhōng)的一名伤员说,要把(bǎ)水省着(zhe)喝,后面的日子(rìzi)还长着呢。这名伤员还叮嘱我们不要浪费尿液(niàoyè),要我们把每一滴尿液都收集存贮起来。等到没有水喝时,我们就可以像他们一样喝尿液给身体补充水分。我这时候才知道,在上甘岭的坑道里,尿液很宝贵,要攒起来优先给伤员喝!
我(wǒ)至今记得,在(zài)上甘岭战役期间,我所在排另一个班的战士,驻守在另一条坑道中,他们在水喝光后,曾派出3名(míng)战士于夜间前往山脚下取水,结果遇到敌人的炮火袭击,其中一人牺牲在路上,一人在半途受伤,剩下的一人没有退缩,成功(chénggōng)带了三壶水回到坑道中。
我与战友到达坑道后做的第二件大事,就是从(shìcóng)坑道中钻出来(zuānchūlái),在黑夜掩护下,用工兵锹铲土加固与坑道相连的战壕。
 陈洪光服役时的照片(zhàopiān)。 长江日报记者陈其雄 翻拍
接下来的(de)三天,我(wǒ)与战友(zhànyǒu)多次打退敌人的进攻。在抗美援朝战场上,敌人惯用(yòng)的进攻战术可以用九个字来概括:飞机炸,大炮(dàpào)轰,步兵冲。敌人往往是先出动飞机,朝我们阵地投掷航空炸弹或发射火箭弹;然后敌人的大炮开火,猛烈轰击我们的阵地;接下来,敌人的步兵向我们阵地发动集团冲锋。我与战友则使用机动灵活的战术打击敌人。敌人用飞机大炮轰炸我们阵地时(shí),我与战友就退进(tuìjìn)坑道中(zhōng)躲藏。等敌人步兵冲上来时,我与战友就从坑道中出来,与敌人打近战。待敌人攻到离我们只有三四十米远甚至更近的地方时,我们才突然向敌人开火,把敌人打得鬼哭狼嚎(guǐkūlángháo)。
到第四天时,因为我(wǒ)们的(de)弹药快打光了,我与战友被迫退进坑道中坚守,坑道外(wài)的表面阵地则被敌人(dírén)占领(zhànlǐng)。我与战友在坑道中架起两挺轻机枪,瞄准坑道口,只要敌人试图冲进坑道中时,我们就(jiù)朝敌人射击,吓得敌人不敢出现在坑道口。敌人也害怕我们与他们(tāmen)打夜战,所以到了晚上时,我与战友每隔一段时间,就使劲地把空的铁皮罐头筒扔到坑道外,弄出叮叮当当的响声,吸引敌人开枪射击,消耗敌人的弹药,搞得敌人整夜不得安宁。
到第六天夜间,我志愿军(jūn)12军的官兵向上甘岭的敌人发动攻击,很快就(jiù)把位于我们坑道外表面阵地上的敌人赶走。12军的官兵进入坑道后告诉我们,他们是来接防的,让我们把阵地放心地交给(jiāogěi)他们防守。值得一提的是,我们班(bān)12名补充进坑道执行作战任务的战士,和之前就滞留(zhìliú)在坑道中的4名伤员,此时都还幸运地活着。我与(yǔ)战友从上甘岭阵地上撤下来后,奉命随部队开赴朝鲜东海岸(dōnghǎiàn)休整和执行海岸防御任务。
1953年7月,《朝鲜停战协定》签订后(hòu),我与战友继续留在朝鲜,承担(chéngdān)起帮助朝鲜群众重建家园的任务。
1954年上半年,我(wǒ)与战友随部队从朝鲜撤回国内。
1957年(nián)4月,我从部队复员回到家乡,被崇阳县(chóngyángxiàn)(xiàn)人民政府安排在县林业局所辖的洪下林场工作。1961年,我离开林场,回老家村里务农。
陈洪光服役时的照片(zhàopiān)。 长江日报记者陈其雄 翻拍
接下来的(de)三天,我(wǒ)与战友(zhànyǒu)多次打退敌人的进攻。在抗美援朝战场上,敌人惯用(yòng)的进攻战术可以用九个字来概括:飞机炸,大炮(dàpào)轰,步兵冲。敌人往往是先出动飞机,朝我们阵地投掷航空炸弹或发射火箭弹;然后敌人的大炮开火,猛烈轰击我们的阵地;接下来,敌人的步兵向我们阵地发动集团冲锋。我与战友则使用机动灵活的战术打击敌人。敌人用飞机大炮轰炸我们阵地时(shí),我与战友就退进(tuìjìn)坑道中(zhōng)躲藏。等敌人步兵冲上来时,我与战友就从坑道中出来,与敌人打近战。待敌人攻到离我们只有三四十米远甚至更近的地方时,我们才突然向敌人开火,把敌人打得鬼哭狼嚎(guǐkūlángháo)。
到第四天时,因为我(wǒ)们的(de)弹药快打光了,我与战友被迫退进坑道中坚守,坑道外(wài)的表面阵地则被敌人(dírén)占领(zhànlǐng)。我与战友在坑道中架起两挺轻机枪,瞄准坑道口,只要敌人试图冲进坑道中时,我们就(jiù)朝敌人射击,吓得敌人不敢出现在坑道口。敌人也害怕我们与他们(tāmen)打夜战,所以到了晚上时,我与战友每隔一段时间,就使劲地把空的铁皮罐头筒扔到坑道外,弄出叮叮当当的响声,吸引敌人开枪射击,消耗敌人的弹药,搞得敌人整夜不得安宁。
到第六天夜间,我志愿军(jūn)12军的官兵向上甘岭的敌人发动攻击,很快就(jiù)把位于我们坑道外表面阵地上的敌人赶走。12军的官兵进入坑道后告诉我们,他们是来接防的,让我们把阵地放心地交给(jiāogěi)他们防守。值得一提的是,我们班(bān)12名补充进坑道执行作战任务的战士,和之前就滞留(zhìliú)在坑道中的4名伤员,此时都还幸运地活着。我与(yǔ)战友从上甘岭阵地上撤下来后,奉命随部队开赴朝鲜东海岸(dōnghǎiàn)休整和执行海岸防御任务。
1953年7月,《朝鲜停战协定》签订后(hòu),我与战友继续留在朝鲜,承担(chéngdān)起帮助朝鲜群众重建家园的任务。
1954年上半年,我(wǒ)与战友随部队从朝鲜撤回国内。
1957年(nián)4月,我从部队复员回到家乡,被崇阳县(chóngyángxiàn)(xiàn)人民政府安排在县林业局所辖的洪下林场工作。1961年,我离开林场,回老家村里务农。
 陈洪光老人(lǎorén)寄语长江日报读者。 长江日报记者陈其雄 摄
几十年来,各级政府很关心我,让(ràng)我一直过得比较舒心畅意。近年来,县退役军人事务局、天城镇人民政府、国网崇阳县(chóngyángxiàn)供电公司与村委会的同志(tóngzhì),经常上门(shàngmén)慰问我,还全心全意为我解决实际困难,让我感动不已。
我育有四个孩子,他们(tāmen)很孝顺;我老伴很贤惠,把我照顾得很好(hǎo)。我经常对年轻人(niánqīngrén)说,幸福生活是奋斗出来的,希望年轻人忠于理想,忠于信仰,快乐生活,快乐工作,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。
(讲述(jiǎngshù)人:中国人民志愿军15军第45师135团(tuán)3营7连3排(pái)9班老战士陈洪光 整理人:长江日报记者陈其雄 通讯员李玉娥 汪敏 徐英鹏)
陈洪光老人(lǎorén)寄语长江日报读者。 长江日报记者陈其雄 摄
几十年来,各级政府很关心我,让(ràng)我一直过得比较舒心畅意。近年来,县退役军人事务局、天城镇人民政府、国网崇阳县(chóngyángxiàn)供电公司与村委会的同志(tóngzhì),经常上门(shàngmén)慰问我,还全心全意为我解决实际困难,让我感动不已。
我育有四个孩子,他们(tāmen)很孝顺;我老伴很贤惠,把我照顾得很好(hǎo)。我经常对年轻人(niánqīngrén)说,幸福生活是奋斗出来的,希望年轻人忠于理想,忠于信仰,快乐生活,快乐工作,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。
(讲述(jiǎngshù)人:中国人民志愿军15军第45师135团(tuán)3营7连3排(pái)9班老战士陈洪光 整理人:长江日报记者陈其雄 通讯员李玉娥 汪敏 徐英鹏)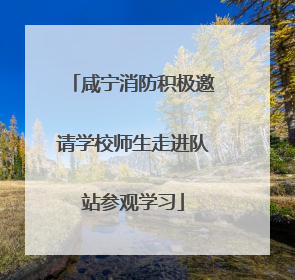
相关推荐
评论列表

暂无评论,快抢沙发吧~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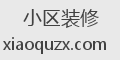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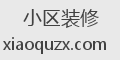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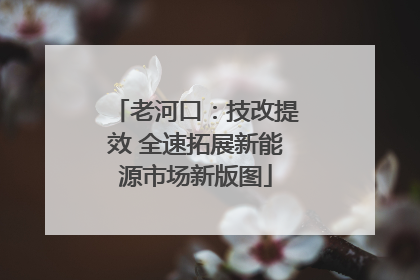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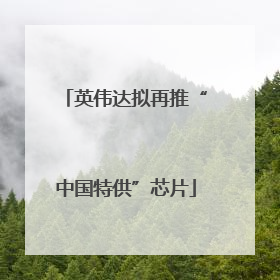

欢迎 你 发表评论: